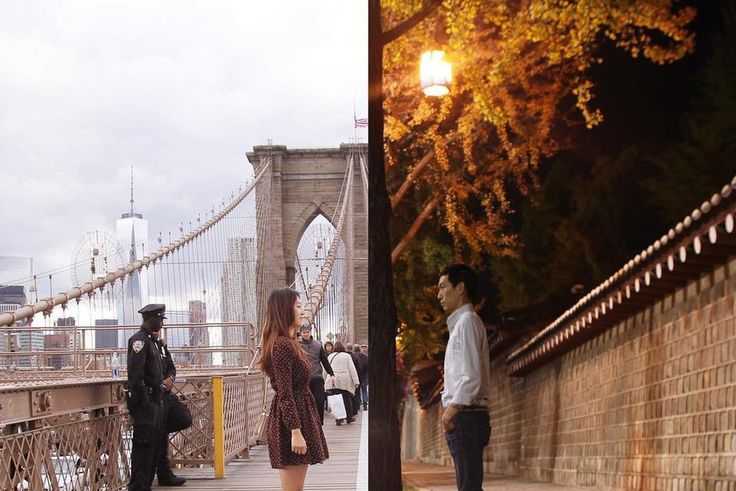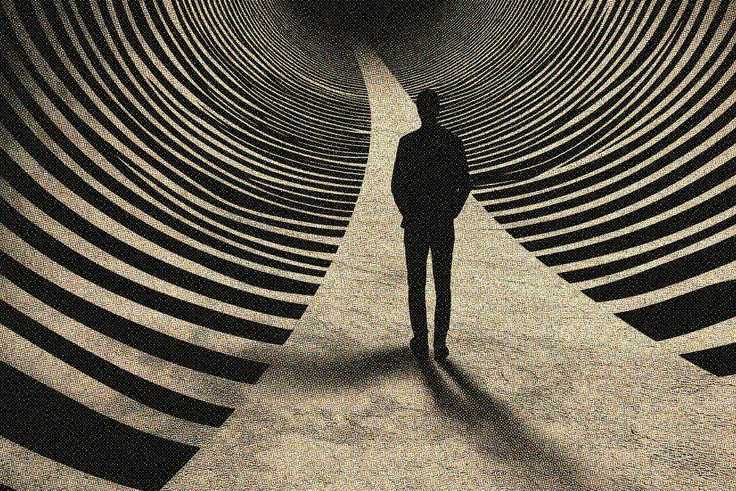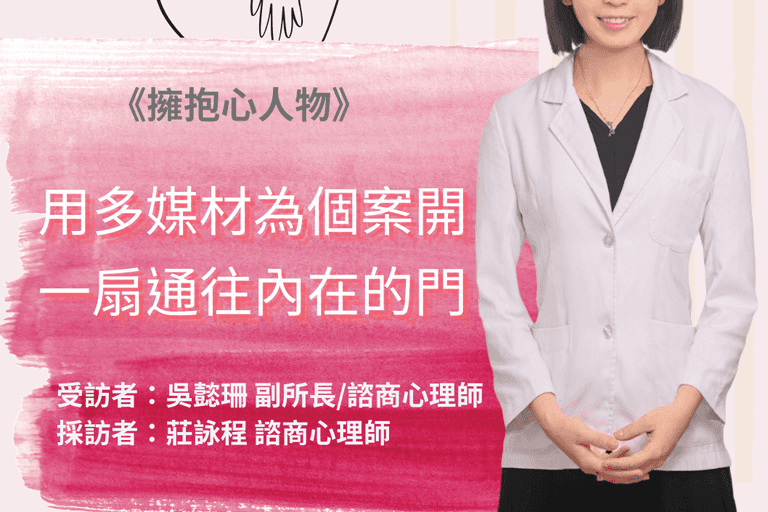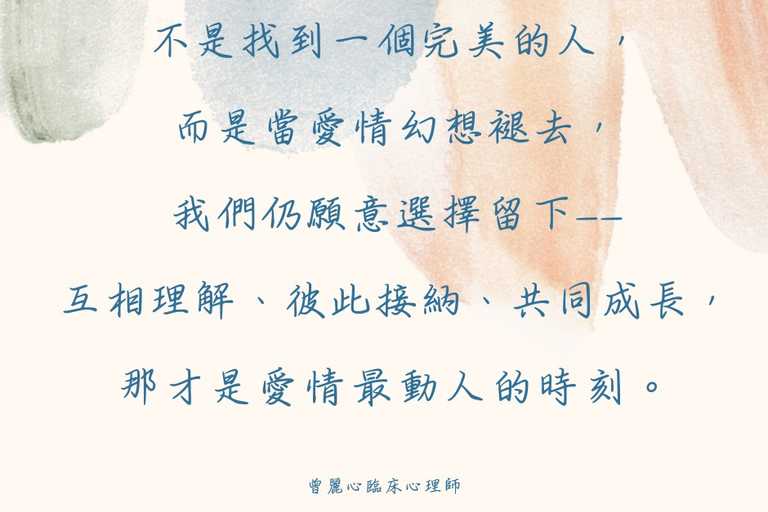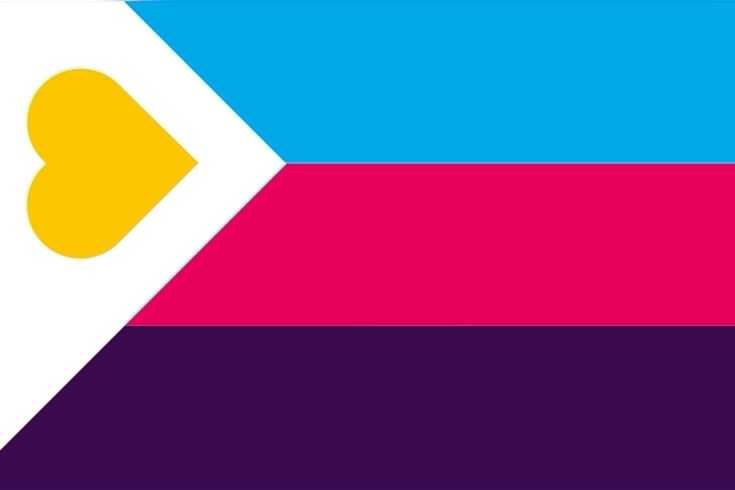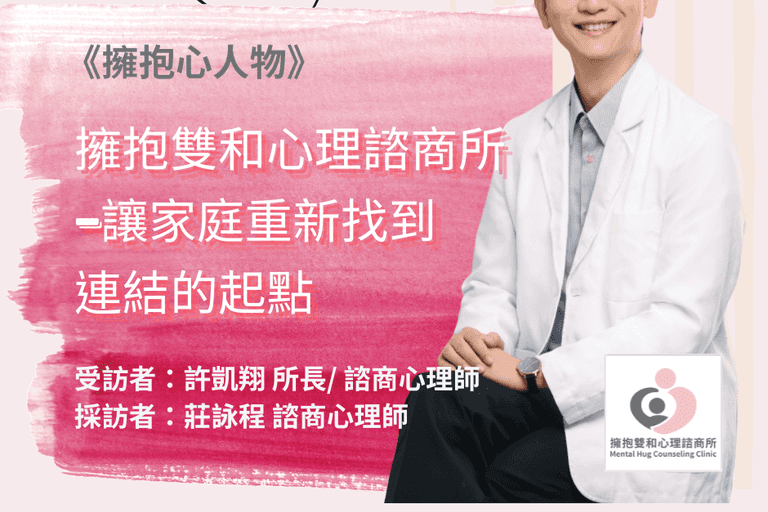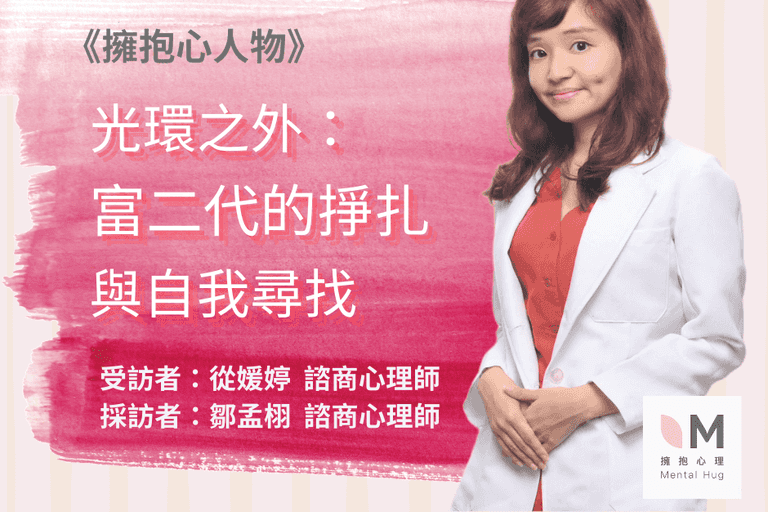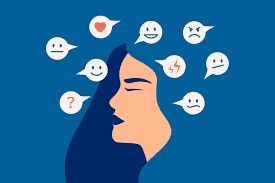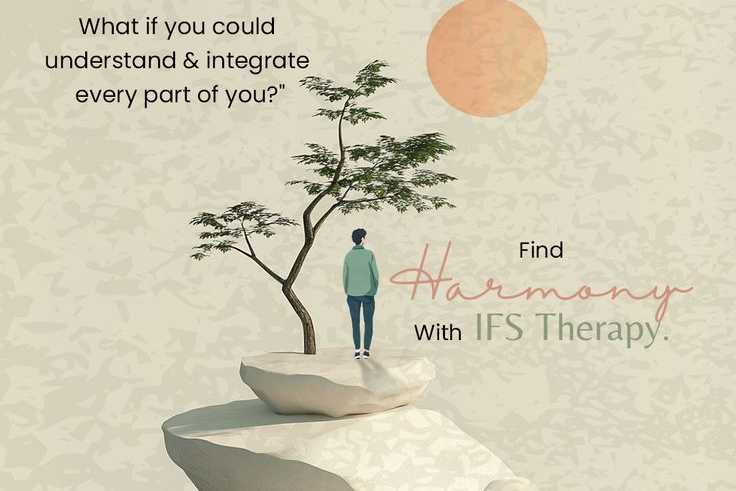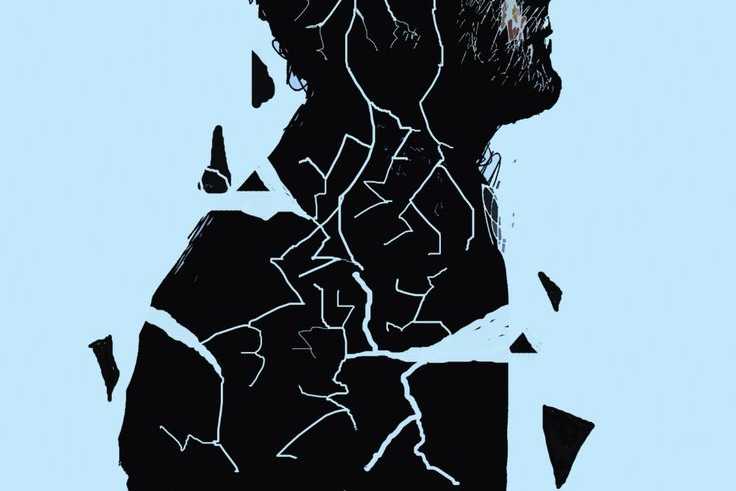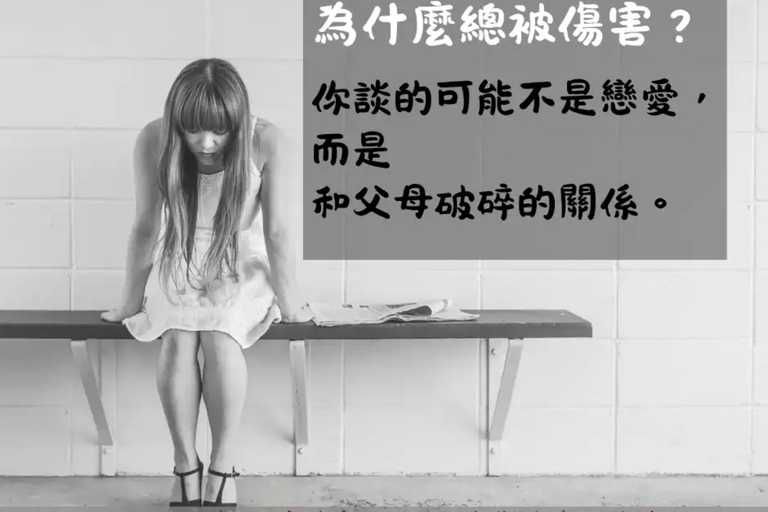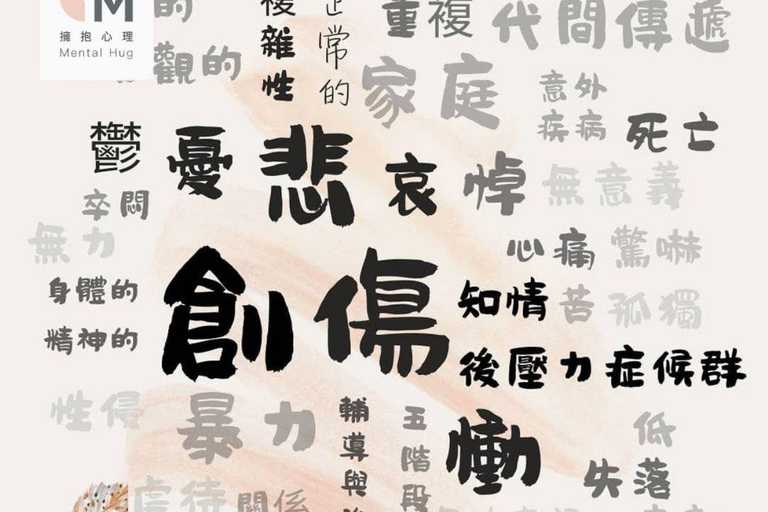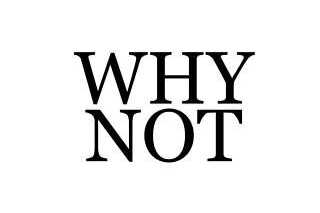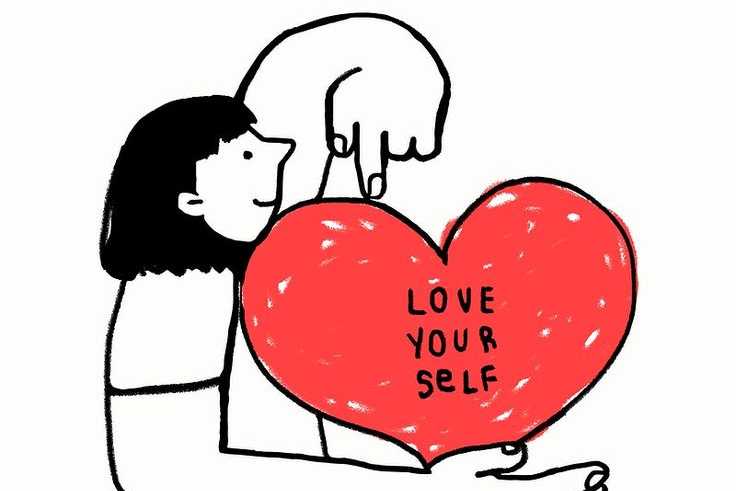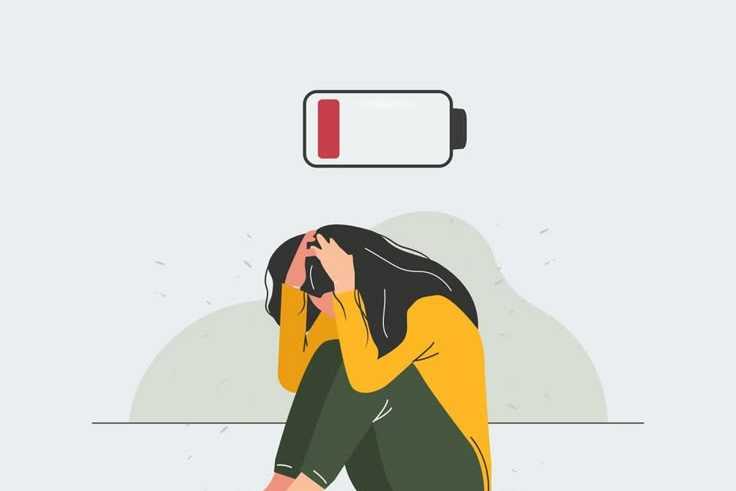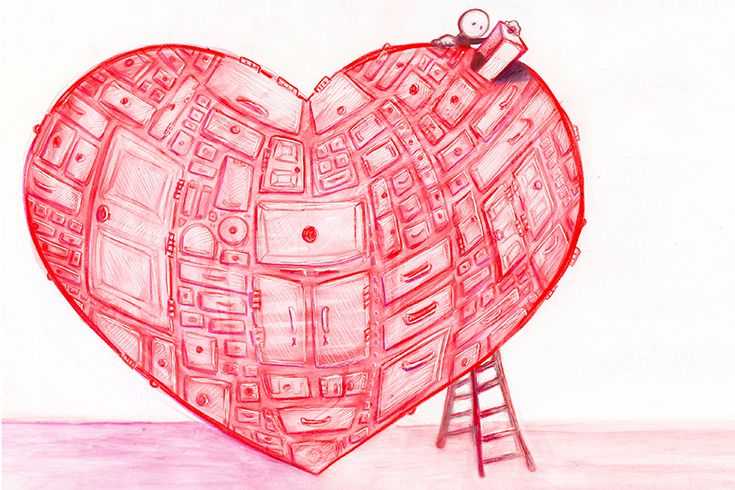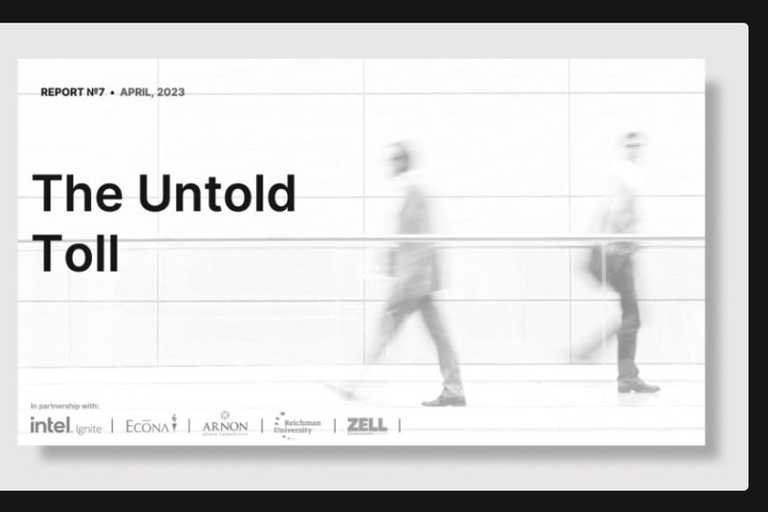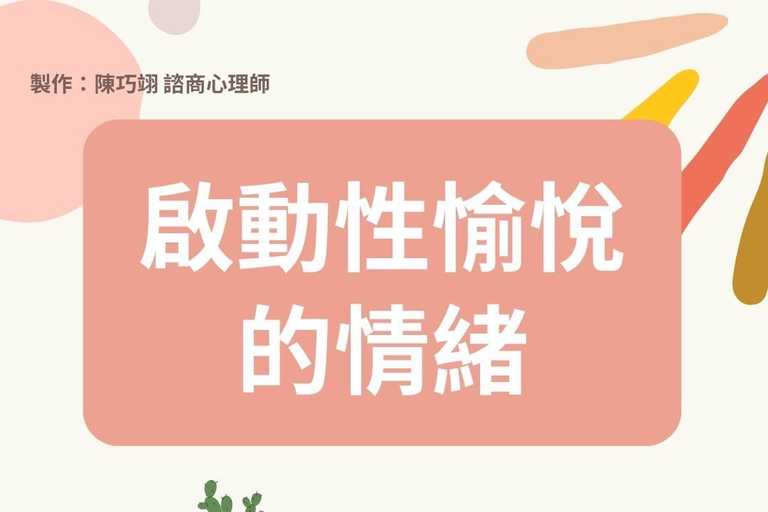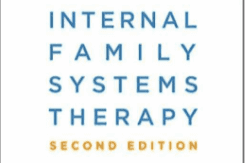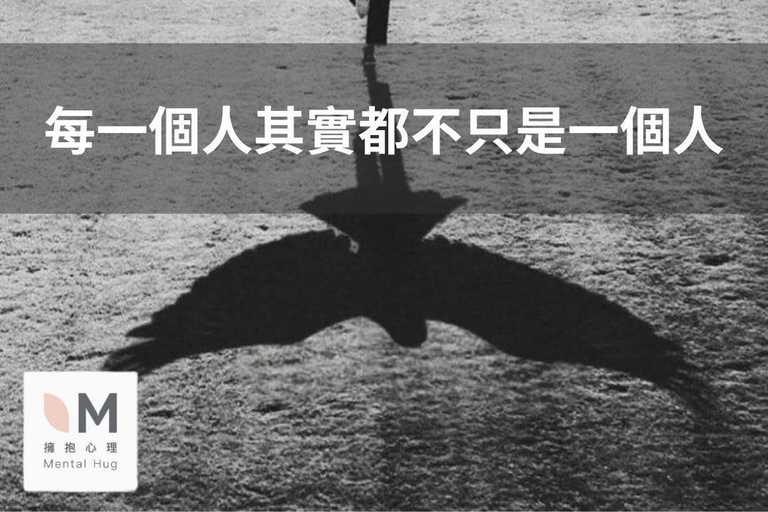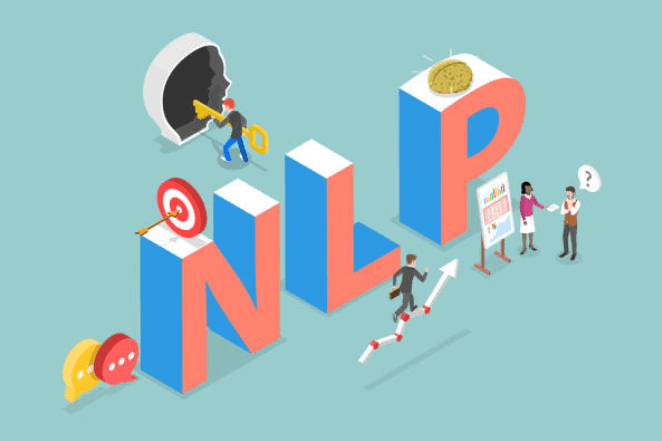為何在女同志的愛情裡,說再見這麼難?探討分手困境背後的心理與社會意涵


徐維廷
2025-07-17發佈
# 桃園心理諮商
# 伴侶諮商
# 台北心理諮商
在LGBTQ+社群文化中,有個半開玩笑的詞彙叫「U-Haul Syndrome」(U-Haul綜合症),意指女同志情侶在第二次約會後就準備搬家同居,關係進展神速。這個詞彙戲謔地描繪了女同志關係中常見的親密與投入。
害怕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伴侶
在LGBTQ+社群文化中,有個半開玩笑的詞彙叫「U-Haul Syndrome」(U-Haul綜合症),意指女同志情侶在第二次約會後就準備搬家同居,關係進展神速。這個詞彙戲謔地描繪了女同志關係中常見的親密與投入。然而,當這份深刻的連結需要走向終點時,分手的過程卻可能變得異常艱難與痛苦。
許多人觀察到,相較於異性戀或男同志伴侶,女同志伴侶在面臨關係困境時,似乎更難下定決心分開。這份困難不僅僅是情感上的不捨,其背後交織著深刻的心理動力、緊密的社群連結,以及獨特的社會文化壓力。作為一名關注多元性別議題的諮商心理師,我希望藉此文剖析女同志分手困境中幾個關鍵的層次。
害怕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伴侶
在一段關係中,伴侶是愛人,但對許多女同志而言,她/他/他們更可能同時是摯友、是家人、是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甚至是對抗外界歧視的戰友。
- 1.支持系統的高度重疊:在一個仍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找到一個能完全理解並接納自己身分的人極其不易。伴侶往往是那個能分享所有關於性向認同、出櫃掙扎、家庭壓力與職場困境的唯一窗口。分手,意味著可能瞬間失去整個核心支持系統,那種孤獨感是雙倍甚至數倍的。
- 2.存在性的孤獨感 (Existential Loneliness):害怕的不是單身,而是害怕「重返櫃中」的孤寂。當生活中最重要的那個人離去,可能會引發一種深刻的恐懼——「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能如此懂我了」。這種恐懼觸及了身為性少數最核心的存在焦慮。
「很難找到新的對象」:迷你的社群與無形的壓力
女同志社群相較於異性戀或男同志社群,在許多地區規模更小、連結更緊密。這種「小池塘效應」(Small Pond Effect)為分手帶來了獨特的挑戰。
- 1.緊密的人際網絡:在一個小社群裡,共同朋友的比例非常高,甚至前任的現任可能是妳朋友的前任。如酷兒研究學者觀察到的,女同志社群中朋友與愛人的界線有時更具流動性,這使得分開後,社交圈的重組變得極為困難。參加任何一場朋友聚會,都可能狹路相逢,被迫面對過去的傷痛與尷尬。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其中一方甚至可能選擇「自我流放」,暫時或永久地離開原本熟悉的社群。
- 2.可見度的匱乏與選擇的稀缺感:客觀來說,潛在伴侶的「候選池」確實較小。這種稀缺感會讓人們在現有關係中更傾向於隱忍和妥協,因為潛意識裡會擔心:「如果分開了,我還能再找到適合的人嗎?這會不會是我最後一次機會?」這種想法會大幅提高分手的門檻。
- 3.社群的「凝視」與污名:分手在任何關係中都是私事,但在緊密的社群裡,卻可能成為公開的八卦與評價。害怕被貼上「又是誰甩了誰」的標籤,或是擔心自己的分手故事成為他人茶餘飯後的談資,都構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
細緻的文化社會意涵:情感深度與角色期待
除了社群結構,更深層的文化與社會因素,也讓女同志的分手過程更為複雜。
- 1.女性社會化與情感勞動 (Emotional Labor): 在傳統性別角色期待中,女性被鼓勵成為關係的維護者、溝通者與滋養者。這種社會化�過程,使得許多女性更擅長也更習慣進行深度的情感交流與連結。著名心理學家 Letitia Anne Peplau 的早期研究便指出,女同志關係非常強調深刻的「情感依附」(dyadic attachment)。當兩個被如此社會化的個體相遇,往往能創造出極其深刻、高強度的情感連結。然而,這種深刻也可能演變為情感交纏(Enmeshment),彼此的界線變得模糊,分開時如同從自己身上撕下一塊肉,疼痛異常。
- 2.內化的恐同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與模範迷思:根據 Ilan Meyer 提出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生活在帶有偏見與歧視的環境中,會對少數族群成員造成獨特的慢性壓力。其中一種壓力源便是「內化的恐同」,即個人將社會對同性戀的負面態度內化至自我概念中。這會轉化為一種「必須成功」的壓力——我們必須向世界、向家人,甚至向自己證明,同性戀情是真實、穩定且美好的。因此,當關係失敗時,打擊不僅僅是個人的心碎,更可能動搖到自我認同。那份挫敗感會被放大成:「看吧,同性戀情果然是行不通的」、「是我不夠好,才會搞砸這段關係,丟了整個社群的臉」。
- 3.缺乏分手的文化腳本 (Cultural Scripts):異性戀的分手,儘管痛苦,但從影視作品到社會論述,都存在著大量的「分手腳本」可供參考。然而,關於女同志如何「好好分手」,特別是在需要共同面對一個緊密社群時,幾乎沒有可供依循的範例。學者如 K. M. Balsam 在其著作中便探討了LGBTQ+族群在關係結束時,所面臨的獨特法律與心理挑戰,凸顯了這個領域指引的匱乏。如何劃定界線?如何與共同朋友互動?如何處理財產與共同生活圈?這一切都需要伴侶在巨大的痛苦中自行摸索,過程充滿未知與不安。
結語:看見困難,是走��向療癒的第一步
理解女同志分手之所以如此艱難,並非要將其問題化或病理化,而是要看見並承認這份痛苦背後的複雜脈絡。這份困難,不是個人的軟弱或失敗,而是身處特定社會文化位置下,必然會面臨的挑戰。
如果你正經歷這樣的掙扎,請記得:
- • 給予自己無盡的溫柔與同理心:承認你的痛,看見你的難。這份艱難是真實的。
- • 尋求專業支持:諮商心理師,特別是熟悉多元性別議題的專業人士,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協助你釐清糾結的情感,重建個人界線,並找到安頓自己的力量。
- • 擴展多元的支持網絡:嘗試在伴侶和共同社群之外,建立屬於「自己」的興趣與人際連結。這能在關係變動時,為你提供穩固的支撐。
說再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女同志的愛情故事裡,這份道別,承載了更為厚重的生命課題。唯有溫柔地理解這份厚重,我們才能在心碎之後,重新拼湊出更完整、更堅韌的自我。
學術觀點與參考文獻 (Academic Perspectives & References)
為了讓讀者對本文背後的理論有更深入的了解,此處簡介幾個關鍵的學術概念與相關文獻:
- 1.少數族群壓力模型 (Minority Stress Model):由心理學家 Ilan H. Meyer 提出,此模型解釋了為何性少數與性別少數群體比異性戀順性別群體承受更高的心理壓力與健康風險。壓力源不僅來自外部的歧視事件(Distal Stressors),也來自將社會負面態度內化的心理過程(Proximal Stressors),例如「內化的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這種壓力會直接影響個人的幸福感與人際關係品質。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
- 2.女同志關係中的依附與自主 (Attachment and Autonomy in Lesbian Relationships):社會心理學家 Letitia Anne Peplau 是研究同志關係的先驅。她的研究很早就發現,女同志關係特別重視情感的親密、伴侶間的平等與深刻的依附感。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中的情感連結強度如此之高,進而讓分離變得格外困難。Peplau, L. A., Padesky, C., & Hamilton, M. (1982). Satisfaction in lesbia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8(2), 23-35.
- 3.LGBTQ+關係的結束 (LGBTQ+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隨著同性關係逐漸獲得法律與社會的承認,其關係的開始、維繫與結束也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學者們開始關注LGBTQ+伴侶在分手或離婚時,因缺乏傳統社會腳本、法律保障不完整,以及獨特的社群網絡結構所帶來的特殊挑戰。Balsam, K. F., & Editors. (2017). LGBTQ Divorce and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Psycholog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緊密的社群網絡 (Dense Social Networks):社會學與心理學研究指出,少數族群的社交網絡通常更為緊密,以提供成員支持與認同感。在女同志社群中,這種網絡的緊密性可能導致朋友與戀人身份的高度重疊,雖然這能提供強大支持,但在關係結束時,也可能引發人際衝突與社交困境。Blumstein, P., & Schwartz, P. (1983).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 Sex. William Morrow. (此為經典著作,雖非專談分手,但對同性伴侶的內部動態有深刻描繪)。
(作者為順性別男同志諮商心理師,專長多元性別與文化適應議題)